发布日期:2025-10-08 11:16 点击次数: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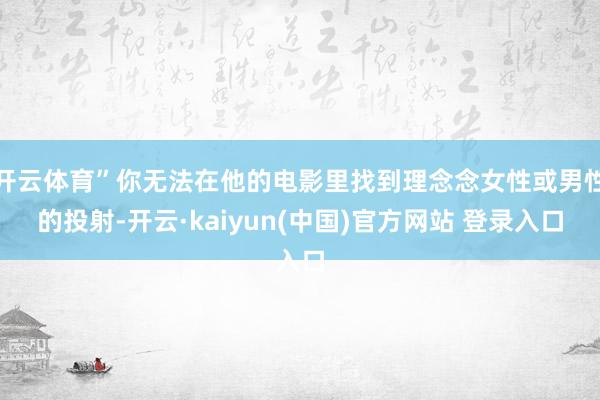
伯格曼的电影有种极为私有的蛊惑力。不,不单是是丽芙·乌曼令东说念主印象深入的推崇,还有更多独属于他的个东说念主象征:灾祸的病东说念主、朦胧不定的神父、死而复生的迷幻、千里默与压抑的脸色,以及各色万般的女东说念主。唯独伯格曼镜头下领有这么的女性扮装,他绝不迟疑地赐与她们自利、颠倒、假心趋赞好意思犀利的疏远,却又因此抵挡灾祸。用特吕弗的一句话:“在他的电影里,女性不是通过男性棱镜反应出来,而所以一种绝对协谋的精神所推崇。”你无法在他的电影里找到理念念女性或男性的投射,唯独清贫而一致的并立与计较,无法得回救赎和自若。
这一切在《呼喊与细语》中达到了极致。
他用一个半小时塑造了整整四位女东说念主,每一位都曾在他之前的电影中有所体现,却并不重迭。玛利亚和《假面》里似笑非笑的女演员,卡琳和《冬日之光》里深受疏远折磨的神父,圣母化身的安娜,伯格曼式的病东说念主艾格尼斯。她们王人聚在《呼喊与细语》,在归并部电影里相遇。
当作段落式的电影,伯格曼能在整个东说念主物都能有劲地被塑变成型的同期敷陈了一个完竣的故事,编剧功底实在了不得。主线索中,敷陈了大姐艾格尼斯病死的现实进程,中间则穿插着护理她的妹妹们和女佣安娜的过往。一切于死者的虚幻推向高涨,又谢世东说念主分割完财产并卖掉庄园,纷繁前去车站后,悲催地亏空。而支线里,老三玛利亚看似关怀亲和,实践沉闷又寂静地渴求情怀,和大夫有不轨之情;老二卡琳在坏话与疏远中抵挡,唯独通过灾祸能力感受到我方的存在;安娜在男儿身后移情重病的艾格尼斯,不教而诛地护理她,是唯独至心实意的护理者,却在她身后被遣离庄园,只是留住了艾格尼斯的日志。电影在日志往常好意思好而平定的回忆中遣散,一切仿若过往云烟,余韵久久不散。
本片很大一部分魔力来自命锁又干净的照相构图,它不仅莫得喧宾夺主,反倒让通盘故事都遮掩着千里默又孤苦孤身一人的颜色。主角们的穿着和环境老是能形成对应,受鲜红墙纸压抑封锁的肉体与白玫瑰般的灵魂,包裹于纯洁的死者对黑衣的生命留恋招呼,遍布着繁复暗纹的餐厅与东说念主物纯洁的相貌,沿路令东说念主印象深入。以下为开场的画面之一

看似静止好意思艳,却和《石榴的颜料》那般透彻的诗电影叙述天差地远,莫得刻意追求静态的东说念主物画。它是动态的戏剧退换与构图均衡的特地蛊惑,沿路是导演所但愿所摆放呈现时画面之上,莫得任何其他要素侵扰。不错从穿着中看到东说念主物的性情:保守而冷情的卡琳,散漫好意思艳的玛利亚,穿着围裙、穿着简朴的佣东说念主安娜。画面右侧的镜子关于世东说念主的注目意味相等彰着。
通常,咱们不错看到奠定全片特色的转场:伴跟着呓语的鲜红渐变面部特写。

文雅·尼克维斯特关于光辉和东说念主物面部特写的特地蛊惑赋予了影片灵魂,针对面部安心而概括入微的捕捉和躁动不安的配景细语带来了热烈的对比。我看完影片许久,每次回忆起《呼喊与细语》,第一个念念起的依旧是鲜红的转场和毫无姿色的脸,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千里默与抵挡的东说念主物情怀。莫得任何一部电影在每一幕的过渡能让我印象至深于此种进程。
至于面部特写、演员演技和台词的最好蛊惑,则是在大夫在镜子前对玛利亚形容她相貌特点的段落。他仔细形容玛利亚的见解、嘴唇、额头、耳朵到下巴的线条,说她现时徬徨、不悦、疏远、粗率与懒散。终末问:“玛利亚,你为何老是冷笑?看到没?你老是冷笑。”不论是演员随大夫的指尖献艺的概括面部动作,如故台词文本中层层递进的假造节拍,都在说出他说出冷笑一词时给我带来了刹那间的震颤,仿佛窥见了一个灵魂的本体。而玛利亚的复兴让这种片面的注目一下变成了两个东说念主的阐述。她说她知说念大夫是在那儿看到了这一切,是在他我方的脸上,因为他们是如斯相像。区分在于大夫认为他们需要被免罪,而玛利亚认为我方无罪,而画面坐窝转到了尤金——被她起义的丈夫脸上。
尤金刺伤我方的那一段献艺也相等精彩,念念到了后世如《牺牲诗社》之类的自尽戏,依稀认为伯格曼在这里的交接有些反高涨。他不仅让一直千里默恇怯的东说念主一边战抖一边喊“救救我”,还以固定的机位捕捉了他慢慢起身、自大匕首、挪到椅子上启动剧烈哽噎的全进程。仿佛不雅察者毫无知觉,只是是一个客不雅存在视角。
画面一瞥,咱们看到了玛利亚懦弱后退的姿色。这和她在艾格尼斯发病时用劲捂住脸时的推崇一样,与遣散最终的潜逃险些如出一辙,疏远的东说念主物形象展现得大书特书。
劣势重重的玛利亚和卡琳让我难以讨厌,伯格曼也并莫得在批判她们。他的电影并不辛辣,而是千里默又克制,险些看不出赫然的脸色倾向。多半复杂和抵挡的扮装,却悠闲无比,仿佛被厚厚的墙壁封锁在疏远和并立的乌托邦。
八成在质询天主上会反应的相比彰着吧,靠近艾格尼斯的尸体,神父的面部却勾出了一个极快的冷笑。
他感叹艾格尼斯比他信仰坚毅,干系词即刻启动评述葬礼事项,仿佛只是例行公务。安娜身为女佣却远比他更像神职东说念主员,致使是圣母的化身,就像《冬日之光》里女西宾远比确切的神父更富于悯恻。在安娜解开领口爬到床边,搂住艾格尼斯的片断,画面最终的定格和名画中的圣母构图如出一辙,在遣散也唯独她粗莽站在故去的艾格尼斯身边,把咱们带回也曾的回顾里。
艾格尼斯在虚幻中的招呼让东说念主印象深入,极有爱伦坡的哥特式主角因为灾祸地留恋着东说念主世的温情即使身躯败北仍不肯离去的异样好意思感。在《野草莓》的开场,主角也在虚幻中见到了起死复活的尸体,在《假面》的开场,小男孩起死复活,走向稠密的恍惚不清的相貌。在伯格曼通常善于推崇咳嗽的病东说念主的难受与恶心的前提下,这种关于生命的留恋就愈加真谛,让东说念主心惊肉跳却豪阔魔力了。重病的艾格尼斯在用她漏风般的嗓子咳嗽时,关于身段泄气出臭味的防卫时,也曾尸体僵硬却仍然一声声招呼姐妹们,致使拥抱玛利亚之时,这一切都让东说念主汗毛倒竖,胆战心惊。说真话,不论伯格曼的演员是什么派的献艺秩序,我这个不雅众一定是彻里彻外成为了一次体验派……
搀杂着呓语与招呼的鲜红转场、封锁的深红壁纸和纯洁的长裙、阴黝黑的死者、开朗的金色公园。电影让咱们体验一场又一场不同的东说念主生,而《呼喊与细语》把我带入存一火的界限,留住难以散去的怅惘。(陈楚晴)
 开云体育
开云体育
Powered by 开云·kaiyun(中国)官方网站 登录入口 @2013-2022 RSS地图 HTML地图